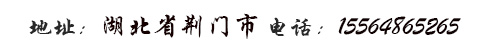何建辣椒糊锅巴子
|
辣椒糊锅巴子 何建 上高中的女儿每次周末回家,总让我给她改善一下伙食,所谓的改善,做的不是鸡鱼肉蛋而是一小碗辣椒糊和锅巴子。妻子总说女儿生就的是穷命,而我很欣慰,欣慰的是不仅女儿喜欢吃,更因为辣椒糊和锅巴子是我心里的念想,这个念想就奶奶,还有度过我童年的村庄。奶奶在我十五岁时就去世了,至今已有二十六,在我很小的时候,母亲在小镇的卫生院上班经常忙着工作,整个童年都是奶奶带我长大的。在我小时候每天早上奶奶必的一碗辣椒糊和锅巴子,也是村里人常做的早饭。后来开始上学了,我也就离开了村子跟着母亲搬到小镇的卫生院居住。那时整天盼着周末,一到周末放学我都要跑着六里地回到村子,一是想奶奶;二是想吃奶奶做的辣椒糊和锅巴子。现在女儿的想法和我小时候有点惊人的相似,所以每次女儿吃我做的辣椒糊和锅巴子时,我都有点激动。女儿吃的不仅是食材,吃的是一种亲情的延续。 辣椒糊严格意义上不叫饭也不算菜,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那是农村人冬季里真正下饭的菜。辣椒糊一般都是早上做,做法很简单。先在锅里放少许猪油,那时淮北一带的农村很少吃到植物油,猪油也很稀罕的东西,所以只能少许,待油化开后放点葱花和切碎的辣椒,翻炒两下迅速加入一瓢水,滋的一声!葱花的香和辣椒的辣在凉水的激发下得到升华,发挥极致,通过空气迅速雾化般传播,沁人心肺,整个厨房里都有一种刺眼刺鼻的香辣味飘散,每次我在厨房时都会被呛得眼睛出泪眼然后打几个喷嚏。几个喷嚏的让我,鼻脑通窍,神清气爽。水开后放点盐加入点面糊翻滚几次后,一碗辣椒糊大功告成。那时农村还没有味精及其他香料,辣椒糊就像村子里的人一样质朴。原始的面香和野蛮的辣味伴随漫长的冬季。 辣椒都是自家在田间地头种的,在秋季里采摘下来,用细线穿起来放在房檐下晒干,每家都有几串红彤彤的煞是好看,也是全年的主要食材。几串辣椒要吃到来年的秋天,放入多少辣椒要取决于每个家庭的经济条件。因为做辣椒糊用的面糊是小麦面,也叫“白面”,白面是稀罕物,做出馍叫白面馍,村子里没有几家能吃上白面馍的。一般都做锅巴子,锅巴子是用红芋面做的,农村一日三餐的主粮就是红芋,城里人叫红薯,当时流行一个顺口溜“红芋面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”。红芋面发甜不适合做辣椒糊。一般都用白面。物以稀为贵。家庭条件好的做辣椒糊时辣椒会少放点,多加点水,多拌点面糊,不是太辣,这样一家就可每人用碗盛半碗,蘸着就锅巴子吃。条件不好的家庭是要多放一个辣椒,为了省白面一家人只做一碗,贼辣贼辣的,不能多吃,一碗就够一家人蘸着就锅巴子吃。锅巴子做法也很简单。红芋面加水活好,待锅里加水烧开后,两只手蘸水挖出一个小面团,边蘸水边拍打面团,不蘸水红芋面发粘会粘手。待拍打成巴掌大迅速用力拍到锅檐上,一直持续下去。奶奶做锅巴子是很是娴熟一盆面在霹雳啪嗒的声音中分分钟贴完。红芋面不能做成发面,而且用篦子做成的饼子非常粘手,自然而然的诞生了锅巴子,锅巴子出锅后一面带焦用手托着吃既不粘手又带点焦脆。红芋面做成锅巴子特别甜,但吃多了会甜的发腻。农村人总要多吃点干活才有力气,此时的辣椒糊在嘴巴里,咸辣掩盖了锅巴子的甜。既让人多吃又不发腻,吃到肚里是暖暖的,驱散着冬季的严寒。而锅巴子的甜中和辣椒糊的辣,吃饱后嘴巴回味总是甜的。我想这也是一种完美的结合吧。 后来搬到城市工作,紧张忙碌的快节奏,很少有时间做早饭,偶尔尝过几家农家乐早点的辣椒糊和锅巴子,味道已经偏远。浓厚的香料和鸡精已经掩盖了,那种物质本身的味道。所以每到周末我都会为女儿做一碗辣椒糊和锅巴子。女儿享受着她喜欢的味道。我享受着对村庄的眷恋和对奶奶无尽的相思。 何建,年人,安徽亳州市人,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,亳州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;亳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;《亳州晚报》特约记者。现供职于亳州市谯城区华佗镇卫生院。热爱文学创作;散文;小说;诗歌;民间故事余篇散见于《亳州文艺》《北方文学》《青年文学家》《亳州晚报》《参花》《西江文艺》。 让阅读无处不在让悦读丰富人生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shuihonghuazi.com/shhzgm/5843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市场白豆蔻八角茴香公丁香浙贝母
- 下一篇文章: 中秋福利想收获延禧攻略同款大猪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