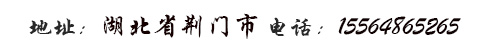麻花子
|
鲁家的满子不念书了,帮着余二老板家卖麻花子。每天早上提着小菜莨子,站在操场边。一下早自习,我们便像离弦的箭一样,冲出教室,冲过操场,冲进食堂。在那个窄小的窗口,递上四两饭票的同时,甜甜地喊一声x师傅或x阿姨,然后伸着带把子的搪瓷缸,食堂师傅往缸子里舀上一勺稀饭。打饭时嘴要甜,喊人,师傅平端着勺子,舀得满满的。碰上脓鼻拉乎的不得人爱的,师傅勺子一歪,分量便少了许多。端着稀饭缸子,一边往回走,一边嘘嘘溜溜地喝。有钱的时候,在满子那里买一根麻花子,四分钱,两个人分着吃。泡在稀饭里,再舀起来,嚼得嘎嘣响,香!挂在缸壁上的稀饭油子,还要伸着舌头舔一舔。在河里把缸子洗干净,锁在箱子里,然后去上课。满子只是静静地站着,从不吆喝。小菜莨子里,麻花子摆得整整齐齐,用红布盖着。掀开红布,让你挑一根,然后又盖上。余二老板,好像只有老夫妻两个,两个都很胖。住在漫水河街头,好像原来是饭店的职工,改革开放了,或是退休了,自己有手艺,炸麻花子卖。满子卖麻花子,一个月挣十二块钱,都交给家里。满子穿了一件水红的的确凉褂子,花尼龙袜子,让我羡慕得不得了。也想不念书了,可是又不敢讲。 学校坐落在河坪里,土坯砖砌的两排教室。靠河的那一排,面南,是初一(2)和初二的两个班。靠渠道的那一排,面北,是初一(1)和初三的两个班。渠道比房顶还高,乱石砌成的石坝,紧邻着教室的窗。上课的时候,我尽琢磨,如果石坝塌了,我该怎么逃跑。课桌是自己从家带来的,五花八门,高矮不一。初三的时候,学校让每个学生上交一段树,梳板子打桌椅。桌椅没打好,我们就毕业了。 宿舍很高级,青砖瓦顶木板楼,有两个天井,两扇大木门是整块的木板做成的,雕着花。后来才知道,这里解放前是马家茶行,生意做得很大。楼下是教师的宿舍兼办公室,楼上是男生宿舍,稻草直接铺在楼板上。不隔音,老师两口子讲的话,学生第二天在教室里学。女生宿舍是后来加盖的一个抱厦,土打墙,既是单独的院落,又有走廊跟老楼连通,单独对外开了一个后门。女生和老师进出,大门后门都可以走,但男生几乎没人走后门。所有的女生住一间,“匚”字形的大通铺,土坯砖作床腿,树段作床沿,床板是树棍子胡乱支起来的,要不杠得脊背生疼,要不掉个大窟窿。食堂的那一溜房,又是另一种格局。墙的下半截,是毛石砌的,上半截是青砖砌的。一座学校,有四种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。食堂有两口大锅,上面加一圈木桶,煮饭也用它,烧水也用它。菜是学生从家带的,吃一个星期。家长中途找机会上街办事,送一趟菜,或者自己请假回家拿。我家里有一口水塘,母亲经常给我送韭菜炒虾子。食堂旁边,沿河是一溜菜地。老师一人分两块,种菜的时候,勤快的学生主动去帮忙,还从家里带菜秧子。我从家里拿了一些苋菜籽给老师,谁知种出来是又高又胖的猪苋菜,丑得招不住。满子拎的小菜莨子,余二老板家的麻花子,是一直想念的味道。寻寻觅觅,再也找不到。某天在超市买了一袋“赵萍麻花”,产地是英山石头嘴。想那余二老板好像也是英山人,这英山的麻花子味道该不差。形状像,味道一点也不像,油味也不像,盐味也不像,香味也不像。将将就就地吃完了。先生以为我喜欢,又买了一袋。看着麻花子,想到了许多事,是年的事。年7月11日星期六,雨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文章已于修改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shuihonghuazi.com/shhzyl/6577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38岁的孙俪近照美呆众人爆料女人一周瘦
- 下一篇文章: 健康一位老中医整理出来的42个秘方,